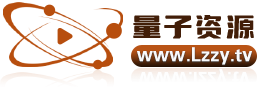女性的代际托举,不止于「出走」 -

(图/《苦尽柑来遇见你》)
有人说,韩剧《苦尽柑来遇见你》一定是东亚小孩吃拼好饭中毒临死前,对完美家庭、完美父母、完美父母爱情的终极幻想。
可当观众从第一集追到最后一集,跟随剧情从1950年代的济州岛到1990年代的首尔,穿越三代韩女几十年的风雨人生,才明白这部剧真正的灵魂,是三代海女在锅台与海浪间的抗争与托举。
1960年,爱纯是饭桌上唯一没有资格吃鱼的人。妈妈光礼接回了她,对她说,「可怜的是我,不是你,不要退缩,要尽情地享受人生。」 1967年,爱纯无处可去,想起妈妈说过,生而为牛,都比在济州岛做女人强。那时候的济州,还在「预防女性离家出走」。 1972年,爱纯掀了让女儿去当海女的祭祀桌,说要让她拥有一切,做一切想做的事,成为可以掀桌子而不是收拾桌子的人。 1994年,爱纯的女儿金明面对未来婆婆对自己出身和能力的质疑和嘲弄,一字一句的反驳回去,要求在职业发展和家庭分工上得到跟男性同等的对待。
三代人,一条路:曾祖母在战前卖汤饭,外婆在水里滚,妈妈在地上跑,女儿才能在天上飞。
我想这部剧之所以能够打动无数东亚观众的心,或许是因为它不只是讲述了一个关于「出走」的故事,更讲了一个关于「留下」的女性主义。它提醒我们:女性主义的路径,从来都不止一条。
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成为李银河笔下的先锋,也不是每个母亲都必须像《我的天才女友》中的莱农那样挣脱原生地。
在现实的土壤里,尤其是对于80、90后这一代女性而言,更多是在锅台边、在育儿室、在职场夹缝中,用沉默的托举,完成着一场静默的革命。
|01 女性主义不该被简化为「出走」
最近几年,女性主义的话题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愈发高频,但它的内涵却时常被窄化为「不婚不育保平安」「逃离原生家庭」「拒绝母职」。
而关于独立女性的叙事,又几乎清一色地绑定在大厂白领、高知女性、海外留学背景之上。她们的故事固然动人,但倘若成为唯一值得被看见的模板,未尝不是一种新的压迫。
而《苦尽柑来遇见你》真正的价值,或许就在于它并没有将女性主义简化成「离开」。爱纯没有逃离济州岛,她留在了那个曾经让她感到窒息的地方,但她改变了它。她也没有成为女强人,但让女儿成为了可以自由选择的人。这种「留下中的反抗」,恰恰才是大多数普通女性的真实处境。
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23年发布的《中国女性发展报告》数据来看,中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虽然已经达到了61.5%,但农村女性仍长期低于50%;而在已婚女性中,超过70%的人表示家庭责任是限制职业发展的主要原因。这也意味着,绝大多数女性并非没有觉醒的意识,而是受限于结构性困境,无法轻易地「出走」。
国内著名的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学者李小江,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一次专访中提到:
我们总是在赞美娜拉的出走,却很少追问她出走之后怎么办?更少关注那些选择留下的女人,她们是否真的就没有反抗?
她说,真正的女性主义,应该是包容不同的选择,而不是用一种「正确」的生活方式去审判另一种。
就像剧中爱纯的母亲光礼,一生困于夫权与贫困,却仍教会女儿不要退缩。她的反抗不是撕毁婚书,而是在饭桌上悄悄把鱼夹给女儿;不是离家出走,而是在深夜为女儿缝制上学的书包。这些微小的抵抗,同样是女性主义的实践。
当社会一味地鼓吹「逃离」时,那些选择坚守的母亲、妻子、女儿,反而成了被遗忘的多数。但她们并不是失败者,因为女性主义的真义,并不是必须要成为谁,而是拥有成为任何人的可能。
|02 母职中的女性力量不应被贬低
在《苦尽柑来遇见你》中,最令人动容的一幕或许就是爱纯掀翻了祭祀桌。那张桌子,象征着济州岛海女文化的传承,也象征着女性世代要被安排的命运。她不让女儿成为海女,不是因为海女不伟大,而是她知道,她的女儿可以有更多的选择。
而这个「掀桌」的动作,经常会被误读为是对传统的背叛。但事实上,更深层的意义是:母亲的爱,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。她用自己的牺牲,为下一代争取了选择的权力。
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「母职」在女性主义话语中的位置。这些年,一些激进的观点甚至将「母职」视为父权制的共谋,认为生育是对女性身体的剥削。这种批判有一定的合理性,但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,就很容易陷入「反生育」的道德洁癖,进而贬低那些选择成为母亲的女性。
但数据告诉我们:中国女性从未放弃过生育。国家统计局2024年数据显示,尽管总和生育率降至1.09,但90后女性中仍有超过65%表示「希望拥有至少一个孩子」。
三联生活周刊在《低生育时代,母亲的选择》专题中采访了多位年轻的妈妈,她们普遍表示:「我不是被迫生孩子,而是想给孩子一个我没能拥有的童年。」
这其中,也暗藏着另一种被忽视的女性主义逻辑:我不是为了延续家族香火而生育,而是为了打破代际创伤而成为母亲。
就像剧中爱纯拼命工作,只为供女儿读书;她忍受生活的折磨,只为不让女儿重蹈覆辙。她的托举,不是顺从,而是一种战略性的忍耐。她知道,自己这一代可能无法飞了,但她的女儿可以。
科学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点。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吉尔·埃德尔曼
(Jill Edelman)
在2022年发表的研究中指出,母亲的情感投入与子女的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。那些在童年感受到被坚定支持过的孩子,成年后更敢于挑战权威、追求理想。换句话说,一个母亲在锅台边的坚持,可能比一场街头抗议更能改变未来。
在一次关于「母职的再定义」的讨论中,女性学者戴锦华也强调过:
我们不能把母职当作压迫的符号来简单否定,而应看到其中蕴含的创造性和抵抗性。一个母亲为孩子争取教育资源、对抗性别偏见、培养独立人格,这本身就是一场微观的政治斗争。
所以,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热烈讨论「要不要做母亲」时,或许更该问:我们如何让做母亲这件事,不再成为女性的枷锁,而成为她们施展力量的舞台?
03日常生活中的女性主义实践
当我们感动于《苦尽柑来遇见你》中女儿金明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时,是不能够忽略真正推动这一切的,是那个始终在厨房忙碌的爱纯。
这也在提醒着我们:女性主义不只是发生在写字楼、抗议现场,亦或是社交媒体上,也发生在菜市场、厨房、学校家长群和深夜的哄睡时刻。这些被主流叙事视为「琐碎」的场景,恰恰才是女性主义最真实的战场。
2023年,中国妇联发布了《家庭性别分工调查报告》,显示女性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为2小时38分钟,是男性的2.3倍。而在双职工家庭里,妻子承担主要育儿责任的比例高达76%。数字的背后,是无数女性在「看不见的劳动」中维持着社会的基本运转。
但这些劳动是否真的就毫无价值?当然不是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·布迪厄曾提出过「象征资本」这一概念:家庭中的情感劳动、关系维护、文化传承,虽不计入GDP,却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一个能把女儿送去留学的母亲,其「文化资本」的积累过程,本身就是一种隐形的抗争。
《苦尽柑来遇见你》中,爱纯不仅供女儿读书,还教会她如何与人谈判、如何捍卫尊严、如何在男性主导的职场中立足。这些「软技能」的传递,远比一张大学文凭更关键。
这也让我联想到了现实中的「鸡娃妈妈」现象。尽管「鸡娃」总是被诟病为教育内卷,但从女性主义视角看,许多母亲正是通过高强度的教育投入,试图打破阶层固化,为下一代争取更多的可能性。她们或许不懂福柯,但她们在用行动实践着「知识即权力」。
很久之前,读到过一位湖南农村母亲独自抚养女儿的故事,她白天在工厂打工,晚上自学英语,就是为了帮女儿辅导功课。最终女儿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,成为家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。这位母亲说:「我没读过什么书,但我知道,只有读书,女娃才能不被人欺负。」
这不是愚昧的牺牲,她知道自己无法改变整个系统,但仍可以拼尽全力,托举女儿站上更高的起点。
女性主义从来都不是要求所有女性都成为女强人,而是让每一个选择都被尊重,每一种努力都被看见。在锅台边熬汤的母亲,在产房里待产的妻子,在家长群里协调活动的妈妈委员——她们或许没有喊出 feminist 的口号,但她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,改写女性的命运。
04 尾声
《苦尽柑来遇见你》的结尾,金明站在首尔的写字楼里,回望济州岛的海。她一定知道,自己之所以能够站在这里,是因为有三代女性在背后的托举。她们有的在水里,有的在厨房,有的在田间,但她们的目光始终向上。
人们常常误以为女性主义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出走,但更多时候,它只是一场静默的接力。有人选择离开,有人选择留下;有人成为先锋,有人成为基石。重要的是,她们都在为彼此争取空间。
根据世界银行2024年数据,中国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9.8年,比1990年提高近4年;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占比连续十年超过男性。这些进步的背后,是无数母亲在灯下陪读的身影,是她们在贫困中坚持「女儿也要读书」的信念。
女性主义的终极目标,不是让所有女性都过上同一种生活,而是让每一种生活都成为可能。你可以选择独身,也可以选择婚姻;可以选择事业巅峰,也可以选择全职育儿;可以掀桌子,也可以修桌子——只要这是你自主的选择。
就像剧中那句贯穿始终的话:「可怜的是我,不是你。」上一代女性的苦难,不该成为下一代的宿命。
所以,别再问「你是不是 feminist」了。更该问的是:你是否尊重每一个女性的选择?你是否愿意为她争取选择的权利?
因为在锅台边熬汤的母亲,和在会议室里谈判的女性,本质上是同一个人——她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,走向更广阔的天空。
商务合作、稿件邀约、媒体专访等事宜可直接扫码添加「刘知趣」(账号原名称:知趣同学)的微信,一起「交个朋友」。